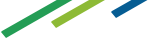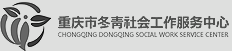(精神卫生项目组 谢馥聪)今年3月底,我毅然辞去了社区工作,来到重庆市冬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始我的社工之路,从事社区精神卫生社会工作领域的服务。在来之前有了解过该项目组主要是服务精神障碍患者,这是一个一直被常人避而远之的群体,也许是受传统观念文化和社会舆论导向的影响,精神障碍患者往往被标签化。其实我并不知道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个群体,只是带着疑问和对社工的热爱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一次和同事到精神障碍患者家里探家访,心理还是特别紧张和担心,也和同事了解了患者家庭的基本情况。小玲(化名)于10年前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身体状况较差,现伴有多种疾病在身,但个人拒绝服用任何药物,虽每天进食很好,身体却越渐发胖;原本和父母及弟弟一起居住,但几个月前弟弟因肝癌过世,现和父母相依为命。这次探访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小玲的服药情况和健康状况,为后续服务跟进做好准备。到小玲家以后,是她妈妈袁阿姨接待的我们;在了解小玲的近况时,袁阿姨说到:“小玲现在基本上已经属于瘫痪了,加上病情不稳定,一时清醒,一时混乱,发病的时候对人就破口大骂,而且连大小便都失禁了,每天都要换好几条裤子……”说着说着她就落泪了,这个时候我竟然发现我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她,我能做的只是默默的看着她,给她递上一张纸巾。这时小玲突然从床上翻过身来说了一句“妈妈,不要哭了。”这一刻,我瞬间就愣住了,我想此刻的小玲意识应该是清醒的,而她也能理解母亲此刻的悲伤,她的一句轻声的安慰比我们说的任何话都更能让袁阿姨宽心。我感叹于小玲的情感表达,也感叹于亲情的纽带是社工关怀技巧里比较重要的一环。
家访完后不久,我们就发现小玲家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持续几天都联系不上她及家人,于是我和实习生一起准备到她家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当我们到小玲家时,却只见大门紧闭,周围邻居也都不在家,回到社工站我赶紧到社区了解情况,询问他们是否了解小玲的去向,第一次这么紧张,特别担心小玲家里发生什么意外。社区也不了解情况,我只能每天都去敲袁阿姨的门,终于在几天后袁阿姨打开了门,但我进屋后却没有发现小玲的身影。原来,我们上次家访后,袁阿姨就考虑到她和丈夫的年纪较大,没有体力和精力照顾小玲,她就四处奔波联系精神病院和养老院,希望她有人可以照顾,最终将她送到了离家较近的养老院,方便探望。袁阿姨说:“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经历了,自从儿子去世之后,孩子他爸爸也自我封闭了,耳朵也听不见,也不和任何人交流,吃饭都要用手比划。”看着袁阿姨眼里的悲伤和无奈,我竟然无计可施。
这次家访结束后,我深深的被触动了。作为袁阿姨,她是要有多强大的内心才能承受生活给予她的这一系列遭遇;而作为社工,我自己的工作要有多失职才使自己没能第一时间陪伴在袁阿姨的身边,支持她去解决生活中遭遇的这些困境。我不停的在反思,我要运用怎样的社工价值和方法这个家庭?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如何与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建立专业关系,使他们再有困难时想到社工或知道寻求帮助的途径?接下来,我又该怎么办?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从社区转入社工服务机构后我的困惑,因为角色和服务方法的转变,我需要更深入的去走进每一个生命和每一个家庭,理解和陪伴他们,支持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社工“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
从一个社区工作者到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身份转换,也许我还准备得不够充分,但是我很庆幸,能聆听和感知这么多生命故事,也希望能通过自己和同工们的努力,让更多精神障碍患者和家庭触及到这座城市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