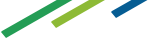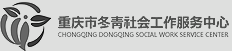(社区矫正项目组 李鸿波)每当谈到父亲,我们总能够想起朱自清的《背影》,月台上“父亲”蹒跚却又坚定的背影,完美地诠释了父爱的质朴与无私。汪柏(化名)是一位六旬老人,两个孩子的父亲,却因诈骗罪被判缓刑5年,接受社区矫正。
2015年1月12日,社工在街道司法所的安排下与汪柏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汪柏身形消瘦,穿着灰色的衬衫,黑色的长裤,头发花白,皮肤蜡黄,低着头,神情凝重。“叔叔您好,我是重庆市渝中区社区矫正项目的社工,是来帮助您的……”社工尝试着与汪柏沟通,听到社工的声音,汪柏慢慢抬起了头,在了解了社工来意之后,开始与社工进行交谈。
“我有一个儿子,30多岁了,我和老伴儿住在一起,我还有一个5岁的孙子……”汪柏带着浓厚的地方口音与社工分享自己的家庭,谈到儿子与孙子时,眉目有少许舒展,转而又变得凝重起来:“我身体不太好,患有精神分裂症,住过两次院了,欠了60万元的债,这一次的事我感到无颜见人,最困难的,是每个月3000元的退休金没了,只能靠老伴儿每月2000元的退休金过日子。”汪柏眉头紧锁,开始唉声叹气。第一次会谈,正如社工第一眼看到汪柏时的神情,是凝重的。
社工心里满是疑惑:一个六旬的老人,何以欠下60万元的巨债?每个月2000元的收入为何不够生活?社工希望能够尽快了解具体情况,并帮助汪柏缓解内心的压力。然而,接下来的,却是漫长的等待——汪柏因为精神分裂症突发入院治疗,一住就是3个多月。
4月22日,汪柏出院后第一次到街道司法所报道,社工得到消息后赶往街道看望汪柏。汪柏是在妻子的陪伴下来到司法所的,在表达时思维略显混乱,其老伴儿告诉社工:“他现在身体还没有稳定,现在就我跟他两个人住在一起,我每天要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哎,因为这件事,他每个月3000块的退休金没了……”汪柏的妻子同样是愁容满面,对于汪柏每月3000元退休金被单位撤销的事耿耿于怀。由于汪柏身体虚弱,第二次会谈匆忙结束,社工仍旧不知道,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年人,究竟背负着怎样的压力?
带着关心,带着疑问,在征得汪柏的同意之后,社工于6月16日前往汪柏住所进行第一次家访。汪柏与妻子住在一个高档小区,电梯房,家里是小两层,这与社工想象中的情形截然相反,只是家里的布置非常简单。经过两个月的休养,汪柏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家中的氛围也令汪柏放松了很多。一阵寒暄过后,汪柏与妻子便开始坐下来与社工话家常。
“这个房子,是我们老两口买的,不过是儿子名下的,反正以后都是他的,所以买的时候只写了儿子的名字。儿子结婚以后,要跟儿媳单独住,我们把三峡移民分的那一套房子给了儿子,花了十几万给装修了,后来又花十几万给儿子买了车,这两年儿媳想投资房地产,失败了,我又去帮忙找人买房子,损失了几万块……”汪柏在讲述自己对儿子的付出时,言语与神情中不是抱怨,而是满足感。
汪柏的妻子则拿来了孙子的照片,与社工分享:”你看这是我家丑儿(化名),我们的孙子,上幼儿园了,但是现在在外婆家。老爷子以前每个月有3000块的退休金,每个月发下来就拿去给丑儿外婆,想让孩子吃好穿好,可是现在一下没了退休金,老爷子觉得对不起孙子。他想去社区找工作,做清洁工都行,可是社区说年纪大了不能去做……”说到此处,两个老人的语气一下子沉了下来,又恢复了以往的沉重。
在后期的介入中,社工得知汪柏还有一个女儿,但从小寄养在农村的亲戚家中。为了尽可能整合力量帮助汪柏,社工与汪柏的女儿晓玲(化名)建立了专业关系,并通过晓玲进一步了解汪柏的状况。晓玲告诉社工:“叔叔(从小管汪柏叫叔叔)总是省吃俭用,从来不让我们给他买一样东西,衣服只穿哥哥不要的旧衣服……”
通过多方的了解和多次的介入,我们不难发现,汪柏是一个付出型的父亲,对子女一味奉献,不求索取,为了孩子,为了家,给自己过大的心理压力,甚至过度透支自己,最终铤而走险,误入歧途,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社区矫正对象以男性居多,他们大部分都扮演了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们有的经营着一个小餐馆,一年365天不停歇;有的每天在工地上挑砖搬瓦和水泥;有的拿着一根棒棒穿梭在山城的大街小巷里,挥汗如雨……他们因为一时的失误或冲动犯了错,但其实跟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差别,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和爱去供养一个家,肩上都承担着爱的负荷。